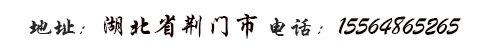黄镛童年趣事
|
时光匆匆,一转眼,我的人生已经跨入了第七十二个年头。回顾一生经历,虽无多大建树,但也非常充实。尤其是童年时的那段经历,深感童趣无限:儿时的淘气玩乐,父母的立规训育,老师的启蒙引导,亲友的关心呵护…至今仍然愰若昨日。 一、从小过继 爸爸妈妈是年结婚的。当时我们家,条件很差很差,祖父给地主家当长工,祖母19岁因患肺病去世,家里穷得叮当响,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,父母是蒲鞋配草鞋结合起来的。东宅顾小施用小车把我娘接来在灶神菩萨前面磕三个头就算完事。婚后日子十分难熬,四年中也没有孩子,一直到年11月8日(农历九月十八日),新中国成立后一月余,盼望多年的我,听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踏着解放全中国的步伐,从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了,而且是一个男小囡。爷爷、父母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,亲戚、朋友也为此祝贺!可我象新中国一样,一穷二白,连生,也生在隔壁的马家宅上。出生后不久,父母为了能顺利地把我养大,专门到浜镇胡瞎子处算命。胡先生说,我的命还算可以,但缺金,要从小过继给人家。因此,就在浜镇找了一家人家(有点亲戚关系),给我取了一个名字,送上了洋碗、调羹。寄爷给我取的大名黄镛从此就跟我走南闯北,迈进了五湖四海。我可能命好,从小就把爸妈的优点毫不客气地都拿来了,白皮肤,大眼睛且双眼皮,长得象苏联小孩。因此,爸妈从小宠我,邻舍隔壁喜欢我,据说我的马永才寄公(房东),只要从上海一回来,就把我抱在大衣里,他们都叫我小外国人,苏联娃娃。 作者童年照片 二、上海滩上 我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去上海静安区胶洲路表姑娘家,从长兴镇到南门码头都由公公小车子送。那时从崇明去上海每天只有一班船,下午一点开,船要开四个半小时。因船小,如遇风大,船摇晃得很厉害,不少旅客晕船,有的还要呕吐。我不晕船,还觉得好玩,有点幸灾乐祸。免不了被妈妈骂几句。船,上海靠十六铺大达码头。下船后一般由爸爸接我们后,坐三轮车去表姑娘家。踏三轮车人穿过人民路、金陵东路,再从浙江路、北京路到胶洲路。夜上海人山人海,灯火辉煌,目不暇接,乡下小囡难得到大城市,通过看、问、了解,慢慢知道了十里洋场南京路,知道了第一百货商店,第一食品商店,亨得利手表店,大世界的哈哈镜,上海古刹--静安寺。我一面看,一面和爸妈聊天,一会儿就到表姑娘家了。 经过5个多小时的舟车劳顿,到表姑娘家一般要晚上6点半至7点了,虽然路上、船上吃过一点妈妈在家里做的糕饼圆子蛋充过饥。但这时也有点饥饿感了!姑娘从小就宝贝我,从来不叫我大名,一直叫我镛囡。我一到,不等我开口,她就开始她的“小偷”行动了(她们家在胶洲路号开了一个很小的烟纸店叫大昌新,前面是店面,中间是吃饭的地方,后间是她公公婆婆的房间,姑娘姑夫的房间在小搁楼上)。她悄悄地下楼,声音的没有,看看柜台橱窗门锁了没有,如果没有,那就对不起了!三下五除二,拿了几个蛋糕上楼请我们娘俩用点心了。(她知道蛋糕是我的最爱)。当然,纸是包不住火的,第二天早上,姑娘挨她公公的一顿骂是必然的。“昨天晚上,那一只大老鼠又偷蛋糕了”?姑娘闷声大发财,不说拿也不说没拿。等到我下楼叫老人公公时,他啊心里也就明白了!原来是这只小老鼠来了!也就不吭声了!因为,他也从心里喜欢我。据说我小时候嘴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与姑娘的感情愈来愈深,我称呼她时由姑娘变为亲姑娘。 上海胶州路号《大昌新》烟纸店的原址 姑娘生了四个儿子,和乐、小平、阿三、小四,他们都比我小,都叫我黄镛哥。我们从小就是铁哥们,懂道理,讲义气,从不吵闹闯祸。我们一起在施家好爹(姑夫)的水果摊看他削甘蔗皮,在弄堂口右边,专门修皮鞋的小皮匠边上的空地处和弄堂口左边,长脚的生煎馒头摊边,一起玩耍;在弄堂里听号的毛里爷叔讲香港的故事,听秃顶、穿着和尚服的郭老板拜佛念经。我们弟兄几个在一起,一直认为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,经常回忆4分一根棒冰、8分一根雪糕、4角9分一包牡丹、4角1分一包红双喜、3角5分一包大前门、2角1分一包青鸟、1角7分一包美丽、8分一包劳动牌的场景。即使结婚成家后,也相互惦念。现在,我们还建了一个“欢乐兄弟情”的群,在网上经常见见面!小时候在上海,还有一件事情特别记忆深刻。上海滩上还有一个特别喜欢我的人,那就是我的黄慕贤好妈,她们家住在南市多稼路,门口就是老式公交车65路的站头。她知道我喜欢吃咸菜洋山芋汤,她顿顿天天烧,我天天顿顿吃,吃到放皮带为止。一时在亲戚圈子里成为一个前仰后翻的笑料。 胶州路原弄的弄堂口 三、水边沟沿 乡下,小时候的故事还真不少。您听到过水桥头上,饭篮里捉鱼虾的事吗?非常有趣。夏天,农村人多的人家早上起来,一般都要在大灶上烧一大镬子的饭,然后盛在用竹头制作的饭篮里,挂在灶间或门口的悬钩上,这样,可以尽快地使饭凉快,饭也不因为天热变质(当然也有钓在井里边的)。第二天,饭篮边上黏了不少米粒,要把它洗净,必须先浸在宅沟的水桥头上,为防止饭篮被风吹走,饭篮上牵了一根绳,这样,小孩捞鱼捉虾的机会来了!那时,生态环境好,清晨,清彻见底的宅沟里,小鱼小虾们争先恐后地到饭篮里来寻食,我们轻轻把绳子拉起的时候,反应慢的就成了我的战利品!一个早晨,要弄一顿新鲜沟鲜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们的高兴劲是可想而知的。当然也有出洋相的时候,自己一激动,人失去平衡,就摔到沟里去了!好在水桥边上水不深,尽管是一只落汤鸡,但还是自己快快乐乐地爬到水桥上,让妈洗刷完毕到家里去换衣服。因为我是大儿子,妈妈很宠,提示我以后注意点就算过去了。 在水边玩的故事还有呢!春暖花开,田里成片成片油菜花盛开,乃是钓菜花鳗鱼的季节,我们用翻地的农具到宅前屋后的稻草底下,碎砖头下面,先挖上一小碗的蚯蚓,然后,用铅丝、线、氽头、竹杆做成钓鱼杆,并在铅丝上穿上蚯蚓,就可以到外宅的沟沿上或泯沟沿上下钓子了,天暖加上新鲜的蚯蚓,钩子下去时间不长,氽头就下沉了,如果您果断地把鱼钩拉起来,一条沉甸甸的鳗鱼就钓上来了!一下午钓几条应该没问题的。当然,更开心的是在排水道里抓鱼。我家宅沟里进出水是靠泥坝下的毛竹管道,毛竹管道到大河里还有一段带坡度的很窄的小沟。每逢天下大雨或雷阵雨,特别是落潮以后,沟里的水急匆匆地从管道里挤着向大河里冲去,您如若在泥坝上静候,那精彩的一幕就会在您的面前出现。“啪、啪、啪”,“啪、啪、啪”,一条,有时几条鲫鱼逆水而来(鱼是喜欢顶水游动的),您只要拿起盆操从鱼尾处向前,它们就成了盆中之鱼。 四、形成规矩 我们的童年就是这样张扬个性,天真烂漫!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二个人,或者说是二个启蒙老师。一个是我的外婆:她一方面给我们整个张家的孙男子侄,外甥男女,带来了白皮肤、瘦高个、高鼻梁、大眼睛、双眼皮,现在说的所谓俊男靓女(这大概就是遗传基因的力量吧)。因为她自身就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。另一方面,她一生带了几十个孩子,那时娘舅、娘姨那家产妇娘临盆,老太太一定提前准备,提前报到,积极参与。说来也奇怪,她手里带出来的孩子个个漂亮,人人聪明。(这当然也离不开外公,外公年轻时是江苏启东汇龙镇一家商行的会计,脑子好用,老板赏识)。外婆不但有一手好的针线活(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逢年过节从里到外穿的新衣服都是外婆做的),能烧一桌好吃的菜,而且一手家务活干得利利索索,了了当当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她烧的大灶上的镬盖一个月,甚至二个月下来,木纹仍然十分清晰。因为她每隔三天,就要用热的石碱水清洗一次。我们兄妹六个都能烧一手可口的饭菜,干一手非常溜的家务活都是从外婆、妈妈身上学来的。她象大家闺秀,说话细声细语,待人诚恳实在。她给我母亲,给我们小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我们在她这种潜移默化的身教重于言教的氛围中,受到了良好的教育! 当然,家教、家规、家风的直接倡导者、管理者、实施者就是我们最亲爱的妈妈了!因为爸爸在上海工作,逢年过节回来也就二个礼拜。因为那时姊们多,家里的所有门摊四费、零用开销都在爸爸一只丁上。他回来时除给妈妈人民币外,也就给我们带点红乳腐猪头肉,这宝贝,色香味齐全,大家一看到就唾涎三尺。一到吃饭,大家筷头向前,毫不客气,吃得打巴掌不放。过一段时间,大家就盼望爸爸回来,希望再次能够一饱口福。他呢,也不管我们太多的事,一年到头,辛辛苦苦,回来就享享天伦之乐!妈妈对我们姊们六个教育极其严格,出去不能直呼其名,要有孙幼长辈,叔叔就是叔叔,妈妈就是妈妈,在家哥哥就是哥哥,弟弟就是弟弟,兄妹间要互敬互爱,互相帮助。就连吃饭,妈妈也教了我们不少规矩:如吃饭不能吃出声音,夹菜只能在自己的一面夹。她说,一碗菜有八面,对着自己的地方才是夹菜的地方,到别人的地盘去夹菜就是这家孩子少教养。眼睛老是叮着自己喜欢吃的菜和满大碗地抄菜都是没规矩。妈妈同时也教育我们,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,不能随便吃别人家的饭。有二件事,尽管过去了6、70年了,我仍然记忆犹新。一件是,我和大妹去东宅小施寄公家去还东西,去时正好在夜饭档子里,他们见我们兄妹俩去,就叫我们吃夜饭。我说,妈妈没有同意,我们是不能在外面吃饭的,可大妹看见几个好菜就自说自话上台准备吃饭了。我一把领头把她从台上拎下来,不管她大声哭叫,带着她就往家跑。当然我的举动得到了老妈的肯定。为了教育妹妹,妈妈打了她一顿,叫她长记性! 另一件事是,有一天下午二、三点钟的时候,我和一群小伙伴到生产队挖红薯的劳动现场去玩。几个长辈见我去了,都非常高兴,其中一个,一边叫着我的名字,一边丢一个大红薯给我,要我拿到宅沟的水桥上洗后吃了!我这时满头大汗,嘴里有点渴,肚里有点饿,她说的话正中下怀。但妈妈在旁边,没有她的许可,我是绝对不能下手的。我只是大声地叫了一声妈妈,没有说任何话,我那聪明的妈妈绝对懂我的意思,她说,这是集体的东西,可以随便拿,随便吃吗?我虽然听懂了妈妈的话,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高兴。于是,弯下腰去,拿起红薯,向她们身边掼去! 五、顺化情结 顺化小学是我初小的母校,也是我接受正规教育,逐步确立人生观的地方。母校坐落在大同大队西边,张网港的东边,校舍极其简陋,南向平房三间,二边二间教室,中间一间教师办公室。因为学生只有来自大同大队和蟠南大队西部的孩子。因此学额严重不足。学校只好搞复式班教育。即一年级、三年级一个班,二年级、四年级一个班,黑板是水泥做的,课桌课椅是拼拼凑凑的,操场上既没有篮球架,也没有其它运动器具,光秃秃的一块场地,只供升旗做广播操用。老师没有住宿的地方,他们是走教(我记得杨士明老师是浜西大队人,李思敬老师是东平大队人,林钟和老师是侯家镇人),即上班是走来或骑着自行车来,下班再照旧回去。几个老师,中午在东边的小厨房里把自己带的饭热一下将就。尽管条件这样艰苦,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,他们的责任和担当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。复式班,一半上数学,一半上语文,一半老师上课,一半学生作业,老师认认真真教,学生卖卖力力学,家庭作业修改,老师也一点不马虎。期中期末考试我们的成绩一点也不比完小平行班差。老师对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很爱,谁有个伤风感冒的,老师会主动关心、主动送药并叮嘱大家多吃开水。我是班长,少先队大队长,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,也会主动去关心同学的学习、生活,同时也去关心老师。记得四年级上半学期,过端午节,同学们把带到学校里来的蛋、粽子分一份出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老师,老师们很高兴。因为,他们感到自己所教的学生的成长和进步。四年中,我也慢慢地接受了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党、爱毛主席的教育。听毛主席话,跟共产党走,逐渐在我们心中扎根。有一件事,至今让我刻骨铭心。年6月1日,这是个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,我光荣地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(大同乡就我一个),团县委组织我们到上海文化广场参加表彰大会,我安排在最中间的位置授奖,给我颁奖的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,陈书记当时问我“小朋友,你是从哪里来的?”我说:“是崇明。”“奥!小崇明,小崇明”!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,可这些场景我还历历在目。从小受到党的阳光滋润,受到党的教育,它在我一生的健康成长中产生了深远影响! 顺化小学旧址 七十年过去了,我和共和国共同经历了艰难的成长历程。我感慨这七十年来的沧桑巨变,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,感谢师长的教育之恩,感谢亲友的关爱之情…这些,都给我留下了珍贵的童年记忆。心语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版权申明:本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anmaoagm.com/etgmks/1246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鼻子不通气怎么办百度经验
- 下一篇文章: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新生攻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