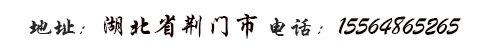晚潮回望
|
本文转自:钱江晚报 □张广智 岁月飞逝,隔着18年的光阴回想母亲的肖像,她蓦然一回望,微笑地看着我,这一影像似乎永远定格在我心中或梦里。 儿时的记忆多已淡化,但有一小事,却让我至今难忘。一天,我感冒发热将愈,妈也厂休在家。她摸摸我的额头说:“烧退了,好嘞。”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后,悄然走出小房间,旋又回头问我要吃什么?我说要吃馄饨。妈二话没说,便拎着菜蓝子出门去采购。小菜场离家很近,她一会儿就回来了,只见灶间:剁肉、拣菜、烫菜、剁菜、调匀、包讫、下锅。不一会儿,一只只馄饨在沸水中翻滚着、跳跃着,好像河中一群小朋友在游泳、在击水。我在一旁看着,差点流出了口水。片刻,一碗热气腾腾的鲜肉荠菜大馄饨放在我面前,青白相间的葱花在碗中飘浮,引发了几多联想。 母亲在沪上一家亚浦耳灯泡厂工作,是个轧丝工,即轧灯泡里的钨丝;在家是位家庭主妇,厨艺精湛。她用灵巧勤劳的双手,点亮了一片星空;哺育儿女,温暖着我们的心,也温暖着世界。这些为母亲点赞的话,那是我多年后写的《无花果树下》一文中的褒语。 “别烫着,慢慢吃。”妈微笑地看着我。稍顷,碗里已吃剩下一只馄饨,我望着妈说:“妈,你也吃一只尝尝。”妈突然被儿的孝道感动,真想领情,于是端起了碗,随即又放下,对我说:“还是你吃吧。”我不从,妈不肯,争执再三,还是我吃了。这个朴素的感性的孝道,被理性的浓郁的母爱阻止了。每每忆及幼时的这件饭事,它虽小却令我刻骨铭心,就此“鲜肉荠菜大馄饨”成了我毕生喜爱的食谱,更是我少不更事时母亲留给我的“胎记”。此后,我不知尝过多少碗鲜肉荠菜大馄饨,总吃不出昔时母亲做的那份味道。 年秋日,我要去复旦大学读书了。儿子上大学在当时棚户区中还少见,爸妈自然高兴,不过对名校什么的,他们全然不知,更何况上世纪50年代的复旦,也没有像今日那样有显赫的名声,更没有想到儿子会在那里生根开花。 母亲说要送我到学校安顿好,我执意不从,这次她被我说服了。步出家门,我背着书包,带着一些书,记得的有两本:未看完的长篇小说《子夜》和翻烂了的长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(李季著),拎一个装有搪瓷面盆、竹壳热水瓶等杂物的网兜,母亲帮我拿一只帆布箱子,衣被尽塞在这个箱子里。 “这箱子蛮重的。”她说,“去学校念书,妈不在你身边得要自力更生了。”这“自力更生”是当时的热词,一如当下的“砥砺奋进”。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工人阶级,对“自力更生”感同身受,妈是个产业工人,自然说得很顺嘴,也契合那时的我。 “会的,会的。”我连连点头。 “同学之间要和气。”她说,“对农村来的小囡,要多帮衬点。” “会的,会的。”我又连连点头。正如母亲所预料的那样,同寝室的H同学,入冬盖被单薄,我告知母亲后,即给他送了一条棉纤混纺的毯子。 我家住闸北区(现合并在静安区)中兴路,离杨浦区邯郸路的复旦大学不是很远,有从北站开出的73路公交车抵达。过了两个街口,73路公交车鸿兴路站到了,她把箱子搬进车内,很快地就有乘客让座,还特地关照一位邻座的大叔,说到复旦大学站下车时请他帮我(复旦大学站有校方助力到各系工作站报到)。秋日的阳光,照在母亲的脸上,她很高兴地望着我,我透过玻璃门窗,也望着母亲。车开了,母亲倒过身子,微笑地看着我…… 母亲在晚年时,一有机会就会跟儿孙辈说起老底子的事,上世纪30年代中期,她首闯上海滩的往事,常常会闯入我的梦中:清晨时,霞光映在她的脸上,挽着梳装得体的舅妈,从弄外拐向武进路,往塘沽路三角地菜场而去;做饭时,灶披间忙碌,舅妈主厨,她是帮手,但厨艺日进,为以后当家烧煮打下了基础;闲暇时,去北四川路(当时称呼)逛逛,北川灯火旺,心里尤舒畅。 然而好景不长,母亲在舅舅家“帮工”的好日子,被“八一三”淞沪战事中止了,只好回故乡避难,直至年冬,带着时年7岁的我再次踏上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。母亲年轻时铸就的虹口“四川北路情结”,似乎有一种莫名的“基因”由我在传承着。不过,我在虹口四川北路安家,这是连做梦也没有想过,但梦想成真了。 母亲渐老似霜降,脸上的皱纹刻着时光的留痕,头上的白发藏着岁月的沧桑,然当她得知我要在四川北路润德坊安家后,无比高兴地对我说:“我老是觉得逛逛四川北路,心里欢喜,走得舒坦,就像老底子我厂出品的亚字牌灯泡,照得心头亮堂堂。”北川灯火照我家,日月如梭,我这一住就是18年,与四川北路结下了浓浓的情缘。 回望,母亲微笑地看着我,不管在世间还是在天上;把回想留给我们吧,放飞梦想,犹如驼铃之于沙漠,灯塔之于大海,希望之于未来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ganmaoagm.com/etgmks/1318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最新石家庄邯郸也延长供热了又胆小又勇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